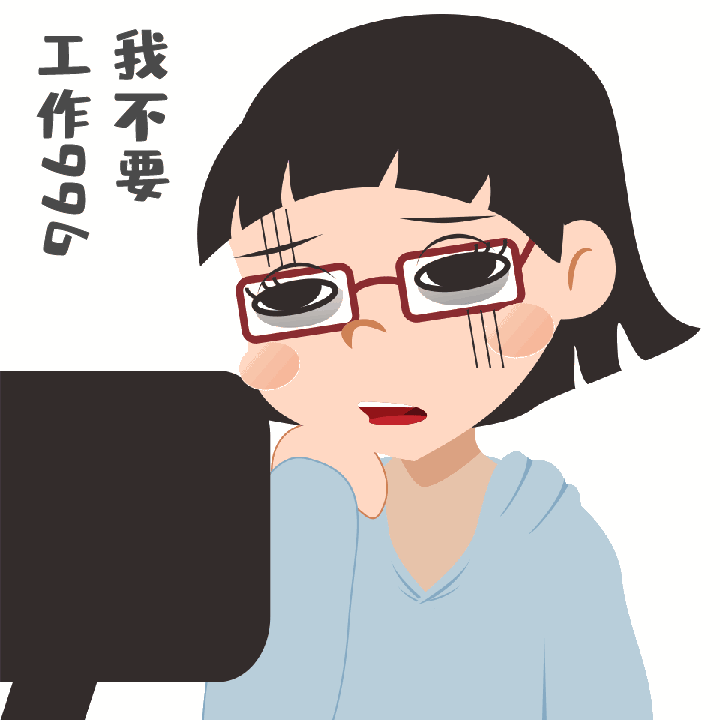本文主要是介绍这位在做游戏的前电影导演,希望能变着法子讲故事,并给予玩家会心一击,希望对大家解决编程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的开发者们随着小编来一起学习吧!
从黎巴嫩到瑞典,从电影人到游戏从业者,这是一位“作者”开发者的冒险
这是又一名瑞典游戏开发者的故事。
区别于大多数安静内向的同行,Josef Fares 因为其张扬的个性而成为为玩家所熟知的开发界网红。他敢在 TGA 直播中脱口而出“F**k Oscar”,敢在开箱危机的风口浪尖为 EA 说话,他创作了两款极具个人风格的独立游戏——讲述兄弟在幻想世界里历险为父亲求解药的《兄弟:双子传说》(Brothers: A Tale of Two Sons),和越狱动作主题的《逃出生天》(A Way Out)。前者需要一人同时操作两个角色解谜,Fares 当时还受雇于 Starbreeze 工作室;后者是两个玩家搭档的分屏游戏,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他带着自己的 Hazelight 团队完成全部制作。两部游戏质量上乘,瑕不掩瑜,足以让主创避开任何质疑其话语权的批评。
这位 10 岁跟着家人逃离黎巴嫩内战来到瑞典的移民,在 23 岁时曾是一名独立电影导演,还上过 Variety 某一年“最值得期待的新人导演”名单。他拍出了基于自身经历改编的、很私人的移民主题电影 Zozo 并拿到了北欧电影协会奖;虽然性格火爆,却又制作了强调双人合作、挖掘角色关系的剧情游戏,内核其实都相当温柔。他一定做对了什么,才能登上全国性的游戏杂志封面、成为游戏头条熟人;才能让自己刚发布了一个游戏的 Hazelight 以独立工作室的身份,与微软 Mojang 等知名公司分享斯德哥尔摩 Söder Mälarstrand 面向沿河美景的办公楼。
个头很高、穿着连帽衫的 Fares,整个人处在相当放松的状态,和媒体上呈现的形象完全重合。他的讲话充满了弹幕式吐槽和不惧主流舆论的坦诚,夹杂着各种同行不会在记者面前丢出的 s**t 和 f**k——“啊,你都开始玩只狼了?Oh s**t,我也要赶紧开始玩……鬼泣?鬼泣算了吧,我觉得它有点奶油哈哈。我最近正在玩地铁,我强烈推荐你玩,太棒了!”
这次更像是闲聊的会面中,我们得以了解一位作者影人-作者开发者的转型,以及他对于叙事边界的追求。自始至终未变的,是他的“创造者”身份。

Zozo(2005)是 Fares 基于自身经历改编的电影,讲述一个黎巴嫩内战中和家人走失的小男孩如何抵达了瑞典
Q=Qdaily,F=Josef Fares,本篇不含游戏剧透
Q:你之前是电影导演,是怎么想到转入游戏行业的?
F:因为我一直都爱游戏啊。在偶然得到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抓住了它。之前人们不太相信我的游戏可以成真,我自己倒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就往这个方向尝试。当时 Starbreeze 工作室想让我帮着导演一下过场动画,我就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做过的一些原型。那时他们还在测试虚幻引擎 3,所以就想着分出一个小组围绕我的原型试一下,其实更像是实验性质的制作。直到后来,这个项目才逐渐变大,变成了真正的游戏。
对于纯粹的电影人来说,做游戏会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你已经看到了好些例子,那些电影圈的人来到游戏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从小就玩游戏的硬核玩家,我当前在做第三部游戏,却依然一直在学习,因为它和拍电影太不一样了,即便是叙事方式——你可以从其他媒介里获得灵感,但你绝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在游戏里说故事。Starbreeze 选择我不是因为我的电影背景,而是我给出的原型很有趣,概念比较独特,每次我告诉人们这个点子,他们都会评价’听起来超新鲜’、’为什么别人之前没想到’等等,你会逐渐习惯的。
Q:《双子》是你的第一部游戏,你有感觉到做游戏比拍电影难吗?
F:难太多了。游戏是互动性质的,电影是一种被动的媒介,你是具备掌控力的,即便拍摄、剪辑这样的工作也很难,但是你做完就做完了,你把它交给观众就完事了。游戏里的观众是参与者,你必须每时每刻地思考他们想要什么、万一他们想做某件事要怎么办……玩家是自由的,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就得跟着他们转。就像是电影观众冲进了片场四处摆弄,你要告诉他们“不不不别动这个”。
以及,你要怎样说故事?电影可以每隔一个时间间隔就开始安排戏剧冲突,游戏不可以,因为每个玩家的玩法不一样,时间掌控也不一样。很多人青睐让玩家自己创造剧情的开放世界游戏,但是我本人更倾向《最后生还者》这种本身拥有剧情的作品,当然它叙述起来也更难。你要探索叙事方式,思考如何利用机制说故事,怎样推进剧情,怎么和别的作品区分。这种带互动性质的叙事,比被动叙述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因为你投入了感情,你真的在行动。


1/3
《双子》中坐下观景时的电影过场效果
这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我刚加入团队的时候总想在机制上实验和创新,幸好有足够有经验的人告诉我那些实现起来会有多难。但是我也十分享受创新机制的过程。在我看来,当代的游戏重复性太强,已经开始让人感到无趣。而且大多数游戏都太长了,当你玩一部游戏时,你很少想到“它要是长点就好了”,至少我 9 成时间都觉得“它应该更短点”。别人也有同感,但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还在让游戏变得更长,而延长它的方式就是更多的重复。
一个游戏在该结束的时候就应该结束,你不能为延长而延长。如今大家都在讨论“重玩性”,但实际上玩家不会去重玩游戏,甚至他们的通关百分比都很小。所以谁在乎重玩性?你首先得让他们把游戏玩完啊。媒体和发行商仅仅是在重复这些概念,他们并不去质疑那是否有效。这就很怪了。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成人哪有上百小时去重玩游戏?每天的新游戏又那么多。当然,如果有上百小时的好故事,我双手赞成,但我不认为现在有游戏可以做到上百个小时一直保持着不重复的高质量。
Hazelight 就试图提供一些不同的东西,尤其是通过我们叙事驱动的游戏来挑战你、让你惊讶,试图让你感到某种情绪,赋予你新鲜感。
Q:所以你的故事点子一般从哪儿来?
F:第一个标准是,我小时候喜欢的那些游戏,比如《塞尔达传说》和《最终幻想》,为我提供了一些思路,但我并不想制作传统的砍杀游戏,我想做之前没人做过的东西,去推动那个边界。我们现在所处的电子游戏世代,赋予了我们太多探索创意的机会,这个领域还十分年轻,还有待开发。而如果你身在电影界,你会发现要做一部不同于其他类型片的作品实在很难,但游戏所处的时代非常好,有很多潜力创意都没被发掘,一切要简单得多。
至于那些想法,我也不清楚从哪儿来,感觉是来自大脑深处,我想它应该来自于个人的激情,是你特别想做某事,对推动边界的渴望,对游戏的热爱……我说不上来,应该是很多东西的结合,它突然就击中你了。
《双子》这个故事虽然是完全虚构的,但也有点我自身的经历。我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一个新生的兄弟,这为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灵感。我想所有游戏,即便是幻想题材的那些,也或多或少来自创作者内心的经历吧。
(你的双人游戏总是包含着“失去”这个元素,你意识到了吗?)
好像是这样。你在游戏中的“失去”其实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失去”,我之前一直在寻思着种种在心理上整垮玩家(mindf**k)的套路,总想让他们大吃一惊。
另外,总是选择两个人,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张力更足,你总是可以创造出有张力的场景,无论是兄弟还是两个合作的囚犯,重点总是“关系”。以及我是个非常热爱叙事的人,毕竟在做游戏之前,那就是我的专业背景。

A Way Out 中的双男主对峙
Q:《双子》中的语言是一种自创语言,玩家完全不明白角色们在说什么,但是也能感受到台词里的情感和力量,这和电影完全不一样。
F:我记得当时我们的预算非常少,还需要自创一种幻想语言,而发明全新的语言体系实在是太难了,最终我选择改编自己的母语阿拉伯语,台词用阿拉伯语写出来,再进行自由发挥,你也许可以从最终的成品上听出一点点阿拉伯语的感觉。而且因为他们在进行实际的对话,他们确实是在表达真实的台词,因而听起来也很真。
Q:发明新语言是因为游戏设定在幻想世界吗?
F:哈哈讲真,因为我们没钱雇英语配音。不过也是因为你很自然地觉得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不该说英语。也许有人认为用大家都懂的语言更能让人感同身受,但是我从来不听别人的话。别人说的事情太多了。说一种熟悉的语言,可能会让你联想到别的东西。
Q:《双子》是单纯的解谜游戏,到了《逃出生天》,几乎什么元素都有一点。
F:对,而且也完全不同。我们现在不怎么见到分屏合作游戏了,更多产品是从不同角色的视角看待事件发展,但和分屏合作还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总是试着做不同的东西,下一部游戏也是,总要尝试着改变花样。


1/3
解谜,动作,冒险,《逃出生天》是一个综合体
我真的不在乎玩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更关心我想要怎样的游戏。朋友可能会推荐我去看某个 Youtube 主播游戏设计相关的视频,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更情愿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清新,听从自己的心声。当然,这也可能是坏事发生的时刻。
《逃出生天》花了我们三年半,那是三年半的痛(打开手机展示动作捕捉的视频),我们要对付所有这些动作捕捉的活……预算相当相当低,70% 的员工差不多都拿着实习生的工资。那游戏看起来像 3A,其实在预算上差远了。我老是开玩笑,我们的预算差不多相当于《神秘海域》的咖啡预算。这是一个相当小的疯子团队,在干一个浩大的工程,目标定得相当高。现在我们倒是有钱了,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可当时是真的难。而且我完全不知道在一个游戏里添加在线模式是这么这么费劲,要花好多额外的时间去写代码,完全出乎我意料。最后半年,我们仍然无法联网游戏,当时都要疯了,差点就决定不搞联网,直接本地联机了。幸好最后还是把它搞定了,这样我们的游戏又多了好多玩家。
不过,整个过程仍然充满了乐趣,虽然也很艰苦,但你事后想想,就感觉像是回忆一段感情生活。你和某人分手了,你之后只会想起这段关系里美好的部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Q:不过你们也得到了来自 EA 的帮助。考虑到 EA (关闭工作室)的历史,这让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忧。
F:是的,EA 也有所赞助。其实当时微软也来找我们签约,不过 EA 提供了更好的合同。为此我感到十分幸运,你不知道有自己的办公室和设备是多么爽。这样我们就能够专注做游戏了,而不是担心运营上的事情。EA 对我特别好,他们无怨无悔,也不加干涉,就让我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我真的很开心。
我知道这对有些人来说很难相信,我也承认 EA 搞砸了一些事儿,但是大发行商不都是这样(f**k up)吗?任天堂也做了不少糟心事啊,可是他们偏偏就是好人形象啊,比如同样的游戏在 Switch 上定价高几倍,他们又从视频网站上撤掉人家的游戏直播。然而没人会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是任天堂。实际上发行商都是一样的贪婪不是吗?微软也好,动视也好,大家都有黑历史。我不在乎合作的对象,只要他们能让我保留创新想法,那是唯一能让我充满激情的东西,没有激情,就什么意义都没有。生命这么短暂,我想尽可能地找乐子。
Q:你是否想继续做电影?
F:当然,实际上我会感到很激动。我从没想过放弃电影,我不想停下做游戏,我两个都要。
Q:你认为游戏界正在发生的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是什么?
F:肯定是关于未被开发的土壤。好多新鲜事在发生,好多技术进步在上演,发展速度是那么快。这是一门特别有趣的媒介,如今能成为它的一部分很让人高兴。开发者需要永远进行革新,这在游戏里永远是关键的部分。
题图来自 A Way Out
这篇关于这位在做游戏的前电影导演,希望能变着法子讲故事,并给予玩家会心一击的文章就介绍到这儿,希望我们推荐的文章对编程师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