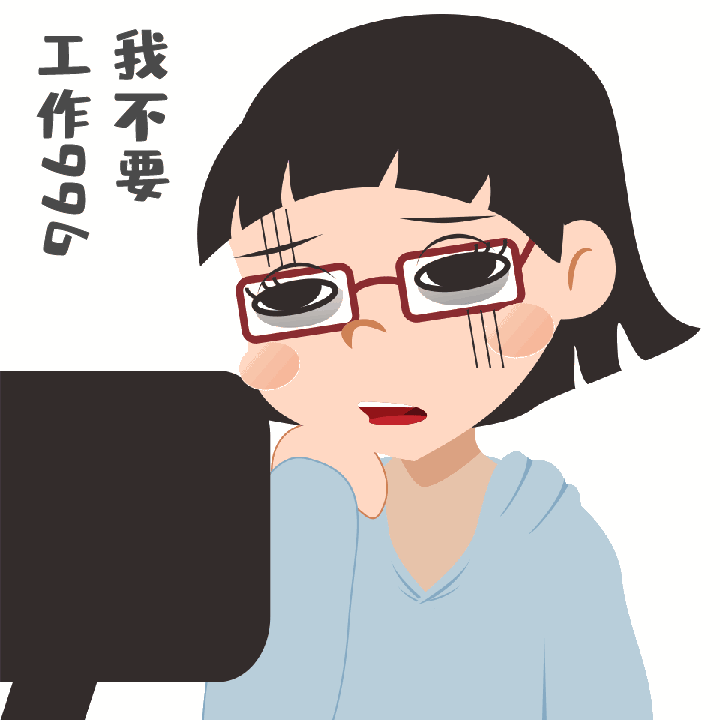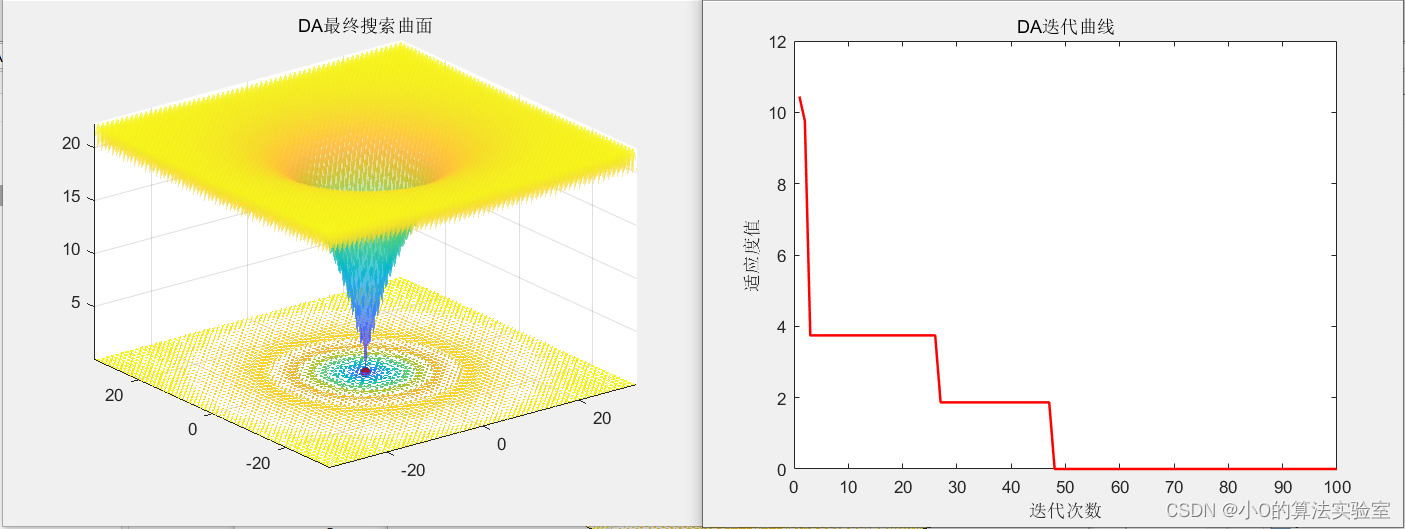芙蓉镇散记
——蜻蜓点芙蓉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我们一行九人连半口鱼汤也未曾喝上,就被导游盯在屁股后面像赶鸭子似的,从长沙、韶山、马王堆、岳麓书院、衡山、张家界、武陵源一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匆匆忙忙,从一个景点奔向下一个景点。
我一直怀疑导游这个职业实际上与导演是同出一门!他们都可以让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截然不同的场景中转换情绪角色。
我们刚才还悠然地徉徜在武陵源天子山的奇峰异峦之间,一个个陶醉得优雅地歪着脑袋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导游却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时间机器将我们无情地匆匆驱赶下了山。不由分说地把我们载到几十公里以外,统统赶进了猛洞河!二十公里的漂流让我们重温了肆无忌惮的童年。
看看自己滑稽的形像吧:雨衣、短裤、赤脚,浑身湿透,水珠挂满了每张兴奋的脸,人人手里拿着重磅水炮,见人就打,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是游人还是艄公,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不管打得赢还是打不赢!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好斗、勇猛、开怀、放纵!橡皮舟在湍流中颠簸,在飞流直下的瀑布中穿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喉头老要嘣出一二句诗来斯文一下自己,却显得很不合时宜。我们在自己歇斯底里的吼叫声中疾速冲过了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上岸,脸上表情极度夸张,毫无保留地大嘴冲着大嘴,相互放肆地观摩着对方大嘴里那个在上颚快乐地荡着秋千的小舌头,“哈哈哈哈哈……”开怀大笑,宣泄、释然,此刻心中所有的世俗和污浊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意犹未尽,“时间机器”却又将我们带入了恬静、舒缓的湘西小镇“芙蓉”,让我们再次经受了短时间内情绪转换的考验。

芙蓉镇,原先叫王村。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早上,那个著名导演一觉醒来,哈欠打了一半,双手还举在半空里突然来了灵感,于是,像大猩猩似地提着裤带拉上靓女酷男一班人马,风尘仆仆赶来,拍了一部电影,叫《芙蓉镇》,从此王村被闹得鸡犬不宁,游客如梭,打破了小镇沉睡了千年的宁静;从此王村被人逼良为娼!当地小官吏,开心得半夜还手舞足蹈,干脆把王村更名为《芙蓉镇》。
我们到芙蓉镇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光景,三三两两的游客使小镇的街道显得格外幽静。尽管小镇已经在二十多年前被那个著名导演破了身子,尽管不再鲜为人知,物欲、喧嚣夹带着都市文明潮水般涌入了小镇,尽管深藏闺中的黄花丫头忽然被强行拽出来曝露在所有的银幕上,尽管小镇如今浑身上下花枝招展插满了各种取媚于游客的修饰,像个初为卖笑的良家姑娘。但是,那些泛着油光的青石坂路,和街道两旁苗族特有的吊角楼以及小镇上人们脸上挂着的代表农耕时代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悠闲、散漫、恬静、舒缓的脸部表情。还能告诉我们,她曾经有过纯朴的历史。




特定的人文,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在精神内容方面的长期沉淀形成的。小镇的人文环境,是农耕时代留下的烙印。当今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了祖国大地的每个乡村山寨,农耕时代的背影距我们越来越远,只留下一些零星的记忆碎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当初那个著名导演的哈欠打完了,灵感没有跳出脑海,即使小镇至今还保持完好的姑娘身,迟早也会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中失掉贞操!和丽江一样,只留下一个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而已。
姑娘虽卖笑为生,毕竟出身良家,尚存些纯朴的影子可以去追溯。从小镇人们散漫的脸上,从慢悠悠移动的脚步声里,从街道两旁一家挨着一家吊角楼的木门缝里,从村子背面传出的潺潺流水声里。我还是拿着相机到处寻找着可以发烧的图片。
我想去拍街背面拍瀑布下的吊角楼全景,得穿过临街的一家铺子,一只脚刚刚迈过门栏,另一只脚还在门栏外面高高地悬在半空里,铺里的姑娘伸出一根纤细白净的手指制止了我。我进退两难,我绷紧了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问其所以然,被告知,出一元钱,便可把另一只脚继续向前迈。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也只能像蜻蜓一样,匆匆掠过那些游走在农耕时代边缘的美丽躯壳。她们已经找不到自己纯朴而美丽的灵魂了,除非那里还鲜为人知,除非那里还交通不便,除非那里还刀耕火种。
叹息,充其量也只是蜻蜓般的呐喊,没人会听见。
来不及太多的叹息,我们又被赶着,去了另一个古镇——凤凰。